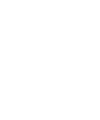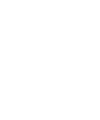为她准备的好躯壳(出书版) - 为她准备的好躯壳(出书版) 第8节
陈逸华摇头:“连默默自己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,我们怎么会知道?她说她从记事起就由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刘氏抚养长大,在我们遇到她时,刘氏刚刚去世不久。”
在王克飞思考的时候,陈逸华抓住机会问道:“可您怎么知道她不是我们亲生的?”
王克飞犹豫了一下,决定把勒索一事告诉陈逸华。事实上,这也是他昨晚思索了很久的决定。
虽然王克飞强调不能证明这封信的真实性,但陈逸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的胸口上下起伏,低声吼道:“为什么会有浑蛋吓唬一个女孩子?为什么默默遇到这么大的事,从没对我说过,也没告诉老师和黄太太?”
王克飞无法回答。如果海默是由捡垃圾的刘氏抚养成人,而刘氏已经死了,那么勒索者和海默又是什么关系?为什么他会用“尽孝心”这个词呢?
“她在近期是否以任何名目向你要过数额较大的钱?”王克飞问道。
“没有。绝对没有。她一向很节省,不喜欢买贵重东西。除了每月给她的生活费外,她极少伸手要钱。”
“为什么您之前没提起收养一事?”王克飞问道。
“我不过是想维护女儿的声誉啊!哪怕她不在世了,我也不希望闲人对她的身世说三道四。”
“知道收养一事的人,应该不太多吧?”
“极少人知道。我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保密措施。幸好我们在欧洲十几年没回国,平时也较少谈及隐私,因此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我和亡妻在海外生的孩子。在收养了海默后,我们立刻回到了欧洲,在那里生活了一年,之后才回到上海定居,为她在震旦女中办了入学手续。我们对外都说这孩子是在欧洲出生长大的。知道真相的只有一些亲人和最亲密的朋友。”大约看出了王克飞在想什么,陈逸华又补充道,“但如果连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过去,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又怎么可能知道呢?”
“那个勒索者应该来自她的过去,”王克飞思忖着说道,“我是指她遇到你们以前。”
陈逸华摇头:“可她自从来了我们家后,和过去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,包括孤儿院的那些人。那个人是怎么找到她的呢?”
王克飞沉吟了一会儿,说道:“也许是她过去生活中的某个人,从选美的报道中看到她的照片,认出了她。”
“八年了呵,”陈逸华苦笑了一声,“你知道一个小女孩从十一岁到十九岁的变化有多大吗?”
他转身从桌边柜子里搬出一本相册,放到王克飞面前,指着一张照片说:“这是我们刚遇到她的时候。”
王克飞端详这张全身黑白照:女孩扎了两条整齐的麻花辫垂在胸口,布衣下的身材瘦骨嶙峋,脸上的婴儿肥却没有退去,两颊胖嘟嘟的,消瘦的肩膀让脑袋显得很大。只有那双眼睛又大又圆,亮晶晶的。
“你能仅凭八年前的记忆和现在的一张照片,就联想到,甚至确定这是同一个女孩吗?”陈逸华问。
不,不能。八年前的孤儿和今天的海默完全判若两人。不仅是因为身体发育后带来的容貌和身材的变化,更多的是整个人的感觉不同了。照片上的小女孩虽然眼睛又圆又亮,却又透着一丝胆怯、羞涩和生活带来的苦相。而在钢琴上、墙上、壁橱上的陈海默却自信、从容、谦虚、优雅,完完全全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的模样。
脱胎换骨。这个词突然闯进王克飞的脑海。
“有了这封信,也许陈小姐的自杀便有了动机……”王克飞小心翼翼地说道,“这也符合您记得的,她离开家那天说的道别话……”
“可我们怎么知道信上的内容是不是真的?”陈逸华朝王克飞瞪着眼睛,“默默年纪轻轻,怎么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过去?”
“要找出这个恐吓过海默的人,就必须知道他所说的‘过去’到底是指什么。”王克飞问道,“土山湾孤儿院的什么人会更了解她的过去呢?”
陈逸华抬起头,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王克飞疑惑的目光相碰。“也许有一个人会知道……”
第15章
“过去”“尽孝心”“偷走的东西”“老地方”……晚上,王克飞辗转难眠,反复琢磨信上短短的几句话。他设想了自己可以走的每一步棋,可能引起的每一个后果——最坏的和最好的。他一遍遍问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放手这个案子。
如果要利用黄君梅提供的线索调查下去,必然需要找到勒索者,调查他口中海默的“过去”。这项工作就好像破坏道路的表面,挖出下水道一样复杂。这么大动静的“工程”怎么可能瞒过黄太太的眼睛?如果把她激怒了,后果会怎么样?海默已经死了,这结果无法改变。为了一个不能改变的结果,赔上自己的前途,值得吗?
或者,他可以就此放手。
如果勒索信一事败露,他可以抓一个醉酒流浪汉当作“勒索者”,随便编造一个调查的结论搪塞过去。只是自己甘心吗?
快早上时,王克飞又做了一个梦。
他站在岸边,看到海默漂浮在黑夜的大海上。她美丽的眼睛像船只的灯光,正在慢慢远去……她将永远地隐没在黑暗冰冷之中。
他明知将永远地失去她,却无法向她伸出双手。
“不,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。”
他睁开眼睛,看着清晨的阳光,对自己说。
早上王克飞起床后,去拜访陈逸华提供的地址——土山湾军乐队领队马承德的家。但在去马修士家的路上,王克飞变得疑神疑鬼,总感觉有一个男人在跟踪自己。
他突然转身走进一家街边的纪念品店,推开门时猛然回头,只见一个穿黑大衣的男子立刻掉头向相反方向走去。因为男子戴了墨镜,又竖起了衣领,王克飞没看清楚他的长相,只注意到他留了两撇小胡子。
王克飞担心这是黄太太派来监视他的人。他兜兜转转在城市里绕了好大一圈,再三确认没人跟踪后,才前往马修士的住所。
马承德虽然有个中国人的名字,却是金发碧眼的德国人。他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,算是半个中国通了,不仅中国话说得好,对中国的文化人情也了如指掌。
他在中国几十年,做的最自豪的一件事是培养了土山湾军乐队。这支隶属于土山湾孤儿院的军乐队并不是他创立的,而是在四十多年前由上海天主教会的一位葡萄牙神父筹募组建的。马承德修士作为任职最长的领队,对乐队倾注了一生的心血。
土山湾军乐队在当年是上海滩最先进和专业的乐队。可谁会想到,这些圆号、萨克斯、军鼓等西洋乐器的演奏者,如此原汁原味的西方交响乐的演奏者,竟是一群衣着破烂的中国孤儿?这些孤儿大多在木工车间或者五金车间当学徒,只是利用下班或放学后的业余时间刻苦排练。许多西方人看了演出,都大为感动。
虽然不再担任领队和车间主任,但马修士依然住在孤儿院里。由于孤儿院是外国天主教会所有,在日据时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。
早晨王克飞敲开他房门的时候,马修士还以为对方只是一个闲极无聊的游客而已。直到王克飞说明来意,马修士才把他请到屋中。待在中国这么多年,马修士早已熟知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规则了。
马修士不喝茶,但他为访客存着上好的碧螺春茶叶,王克飞龇牙咧嘴地喝了一口热茶,立刻开门见山地提到了陈海默。
刚开始,马修士还有点不明所以。但是当王克飞说到“小山”这个名字的时候,马修士多年前的记忆被唤醒了。
“马修士,您能回忆一下当年小山是怎么到孤儿院里来的吗?有什么人会了解她在孤儿院以前的生活呢?”
马修士年事已高,记忆在大脑中变得支离破碎。但那么多年过去了,他对关于“小山”的片段却依然完整地保留着。
见到小山的那个早上,马修士正为孤儿院和军乐队日益增多的开销焦头烂额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,乐队已经具有不小规模,经常在教会组织的各种重要礼仪、庆典中露面。这本是支公益乐队,演出从不收费,最多也就是由邀请方请孤儿们吃一顿饭而已。欧洲局势开始紧张,海外的经费大量减少。淞沪会战一打响后,不少资助孤儿院的教徒纷纷离开上海,经费更是难以保障。马修士正盘算着该怎么给国外的教会写信,才能求得自己需要的资助。
这时,新雇的钢琴师高云清敲门走进了办公室。他的身后跟着一个怯生生的女孩,穿一件缀满补丁的布衫,扎着两条小辫子。
“这是我邻居的孩子,亲人刚刚死了。她一个人无依无靠,我那里也不方便留她,您看,是否能让她留在这里呢?”高云清问。
马修士知道,高云清指的是把她留在五金车间。马修士本人身兼五金车间的主任,每隔几天就会遇到这样的请求。他不得不锻炼出一副铁石心肠,因为如果把每个孩子都接收下来,孤儿院早就人满为患,难以为继了。
马修士感觉到女孩的眼睛亮闪闪地看着自己。他回避了她的眼神,把目光转向高云清,说道:“抱歉,我们不能留她。你知道我们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是男孩。”
“可是,她能做和男孩一样的事情。”
“不,不是这个问题,这是规定……有许多原因……我们要保证男孩先进车间当学徒。”马修士觉得每当自己拒绝别人时,学了十几年的中国话就不那么利索了。
“可您让这么小年纪的女孩怎么办?流落街头吗?”高老师平日里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,此刻的语气却有些激烈。
“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吗?”马修士转向女孩,希望能找到其他办法。
女孩咬着嘴唇摇摇头。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宣判,双眼噙着泪水。
“你之前都是和谁一起生活的?”
“我和刘奶奶一起长大的,”女孩口齿清晰地回答,“但她其实不是我的亲奶奶,她靠捡垃圾为生,在我还是婴儿时把我捡回家了。可是,她上个星期去世了。”
她难过地低下头。
“你就没有其他亲人了吗?”
“我不知道我的爸妈是谁,也不知道其他亲人。”她委屈地抓着衣角,“连刘奶奶也不知道。”
“她真的是走投无路了,我才想到来找您。”高云清紧跟着说。
“先生,”女孩抬起头,提高了音量,“只要您给我一个地方睡觉,我什么活儿都可以干。如果我不能去车间干活儿,我可以替军乐队保管乐器,打扫教堂,还可以给大家做饭——”
“你会做饭?”
“嗯。”她自信地点点头。
马修士皱着眉头,沉默了一会儿。他依然在心底埋怨高云清在这当口给自己添乱。
“那先让她去厨房帮忙,再和你一起管理陈逸华先生新捐的那批乐器吧。”他甩了甩手,“给她找个地方住下,再做打算。”
在打发他们离开后,他才想起来,他还没有问那个女孩的名字。
那阵子马修士满脑子都是经费的问题,也再没有和高云清讨论过如何安置小山。
有一天傍晚他经过乐器室,看见女孩正在努力擦拭那些鼓号。那些崭新的乐器在她的精心擦拭下闪闪发亮。
还有一次,夜深人静之时,马修士经过礼拜堂,听到了钢琴声。是谁这么晚了还在弹琴?他带着愠怒走到门边,发现了女孩的背影。
他吃惊地发现她会弹钢琴。月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上投下惨白的光影,她专注地舞动双手,孤独的音乐如月光般清冷。
他站着看了一会儿,并未上前阻止,而是悄然离开。
之后他几乎忘记了“小山”的存在,直到她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对陈逸华夫妇的答谢演出上。
第16章
自从打仗以后,怎么才能维持军乐队不解散,是马修士最头疼的。得知军乐队陷入了财政困难后,身在维也纳的陈逸华夫妇拿出多年的积蓄,派人捎回国,交给了马修士。马修士用这笔善款添置了小提琴、手风琴等乐器,聘请了钢琴师高老师。马修士一直十分感激陈逸华夫妇的慷慨解囊,因此得知他们回国的消息,便决定为他们举办一次答谢音乐会。
那次先后上台表演的有军乐队和唱诗班的孩子们。坐在台下的不仅有陈逸华夫妇,还有上海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和一些音乐界人士。
演出进行得很顺利。但在谢幕后,观众正要起身离场时,唱诗班的队伍后排突然走出一个个子较高的孩子。她深深地鞠了一躬,一根辫子从帽子里滑落,大家才吃惊地发现这竟是个女孩。
孩子怯生生地问道:“我能为先生太太演奏钢琴曲《致爱丽丝》吗?”
马修士一看,这不是高云清带来暂住孤儿院的女孩吗?他顿时恼火了。唱诗班里都是清一色的慈云中学的男生,经过多年专业的声乐训练,怎么会混进一个都没学过唱经的女孩呢?他急忙抓住身旁的高云清,问他是怎么回事。
高云清却支支吾吾地说,临上场时一个唱诗班的男孩突然腹泻,连床都下不了,他才把小山找来顶替。但他保证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一幕。
“把她叫下来!”马修士命令道。他刚想吐出下面一句“我再也不想见到她”,耳朵里却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:“让她试试吧。”
马修士回过头,看到陈逸华的夫人冯美云笑眯眯的面孔。
“难得有个孩子能独奏,我们倒有兴趣听听她的水平如何,也可以知道老师教得如何。”她慢条斯理地说道。
马修士又把目光投向陈逸华本人征求意见。陈逸华也微微点了点头。马修士忍下怒气,让高云清先允许女孩表演。他想着等一切结束后再处置他们。
女孩欣喜地在钢琴前坐了下来,伸出一双洁白的小手,开始弹奏。马修士的余光注意到,观众席上的其他人都听得专心致志,为琴声所吸引。
表演结束后,陈逸华夫妇和台下的其他观众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,就连高云清这小子也跟着鼓掌。
谁知道下面一幕更出乎马修士的意料。女孩站起来鞠躬致谢时,稚嫩的脸庞上毫无征兆地滚落了两颗泪珠。
她用手背仓促地抹去,哭着说,她一直都是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弹钢琴,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掌声。她还说,她想念她去世不久的奶奶了……这一幕谁都没有料到,看来连那个“同谋”的高老师都有点措手不及。
散场后,陈逸华夫妇要求单独见见那个女孩。他们关心她在哪儿学的钢琴,生活得如何,家人在哪儿……得知她练习钢琴不过两年,他们十分惊讶她的水平。他们的表扬让站在一旁的高老师也沾了光似的,扬扬得意的。
马修士注意到小女孩在回答陈逸华夫妇的问题时谈吐老练。
当她告诉陈逸华夫妇她是多么感激马修士的照料时,马修士的脸色顿时变得很尴尬。他除了第一次允许小山留下外,从没过问过她,更别提关心照顾了,所以,小山所说的那些赞誉之词并不真实。
他并不感激她编造谎言,相反,他惊异于这小女孩是多么懂得影响别人的心理——她一方面用客套话来展现给陈逸华夫妇看她是多么知恩图报;另一方面她又企图通过美言来贿赂马修士,争取他的支持。
后来,陈逸华夫妇邀请女孩和其他几个孤儿去家中做客。大约在两个星期后,他们向马修士提出了收养她的心愿。
马修士知道陈逸华夫妇两人十分喜欢孩子,却一直苦于没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收养孤儿本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,只是,他对他们最终决定收养小山却有一丝担忧。这女孩的身上有一种东西叫他捉摸不透。她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为稚嫩童真的模样,却又透着一种步步为营的气息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